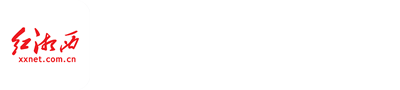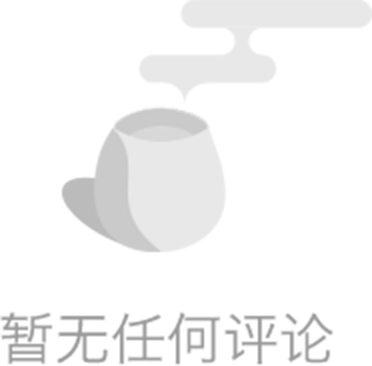《甲骨文字典》“养”字字形及释义。

《土生说字》“养”字释义。
文/图 唐正鹏
但凡读《论语》者,都知道孔子说了这么一句话: 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。殊不知此语一出,便成了千百年来人们诟病和指斥孔子“轻蔑妇女”的“把柄”和“依据”。同时也成了“尊孔派”和“贬孔派”争论的焦点。
“贬孔派”自不必说,“尊孔派”为了维护孔子的声誉,或从文字学、文献学和训诂学的角度,试图在浩瀚的古典文献中找寻依据,全力为孔子辩护。下面略举几例说明之:
其一,“女子”为“越位”与“失德”之女性的全称。汉代三位著名人物都持此观点。杨震说:“《书》诫牝鸡牡鸣,《诗》刺哲妇丧国。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,恣骄弟之情,几至危国,然后加讨,《春秋》贬之,以为失教。夫女子小人,近之喜,远之怨,实为难养。”爰延说:“昔宋闵公与强臣共博,列妇人于侧,积此无礼,以致大灾。武帝与幸臣李延年、韩嫣同卧起,尊爵重赐,情欲无厌,遂生骄淫之心,行不义之事,卒延年被戮,嫣伏其辜。夫爱之则不觉其过,恶之则不知其善,所以事多放滥,物情生怨。”荀悦说:“夫内宠嬖近,阿保御竖之为乱,自古所患,故寻及之。孔子曰: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。’性不安于道,智不周于物,其所以事上也,惟欲是从,惟利是务;饰便假之容,供耳目之好,以姑息为忠,以苟容为智,以技巧为材,以佞谀为美。而亲近于左右,翫习于朝夕,先意承旨,因间随隙,以惑人主之心,求赡其私欲,虑不远图,不恤大事。”
上述汉代名人之言,虽多出自典籍,有一些道理,然细细思之,却有断章取义、牵强附会之嫌,实难服人,故而不足为据。
其二,“女子”为特称特指。以宋代邢昺、朱熹,清代王船山为代表。邢昺说:“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,难畜养。所以难养者,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,疏远之则好生怨恨。此言女子,举其大率耳。若其禀性贤明,若文母之类,则非所论也。”朱熹解释道:“此‘小人’,亦谓仆隶下人也。君子之于臣妾,庄以莅之,慈以畜之,则无二者之患矣。”王船山更是在“女子”之前加上定语“妾媵”,特称的意思更为清楚,看似逻辑性更强。
这几种说法,古典文献中并无“小人”就是“女子”,或者就是“仆隶”“妾媵”的明确出处,故多有臆测、揣测之嫌,亦不可全信。
其三,从文字和训诂学方面解“女”“与”。清代康有为认为:“‘女子’本又作‘竖子’,今从之。‘竖子’,谓仆隶之类;小人,谓人之无学术行义者,兼才臣昵友而言。竖子、小人多有才令人亲爱者,然远近皆难,故不易养,惟当谨之于始,善择其人。”当代一些学者除了在“与”(释解为“与……一样”、“与……共事”、“如同”等)上做文章外,还将“女子”释为“女孩子,女娃子,女儿,青年未婚女性”。 更有人认为:孔子在卫国发现自己不仅被卫国君主欺骗,还被卫国君主身边的小人愚弄。孔子便指责卫国君主听信身边小人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!”于是,孔子离开卫国之后,就发出了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近之则不孙,远之则怨”的感慨。
康氏的说法没有根据,古“女”字属“鱼”部,“竖”字属“候”部,顾炎武虽然将“鱼”“候”归于一部,然仍有区别,顾炎武的归类是一家之言,先秦时期“女”“竖”并无通假和假借之例,虽出自名家之口,但充其量只能是“可备一说”而已。至于将“女子”说成是“未婚青年”更为无稽之谈,没有任何采纳的依据了。
在我看来,孔子说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一句,不仅原因并没有那么复杂,而且伟大的孔子这句话的确说错了!
查阅孔子生平,有三个女人对孔子的一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,即他的母亲颜徵在、妻子亓官氏,以及后来在卫国见到的卫灵公夫人南子。这三个女人不仅在孔子的内心世界有着巨大的反差,也是他对“女子”误判的重要原因。
孔母颜徵在:勤劳贤淑,慈严兼具。据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一文中记载:“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。其先宋人也,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。伯夏生叔梁纥。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,祷于尼丘得孔子。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。生而首上圩顶,故而因名丘云。字仲尼,姓孔氏。”孔子三岁时,父亲去世,与母亲颜徵在相依为命,艰苦度日。这位青年丧夫的母亲,不仅对孔子呵护有加,而且为了让孔子读书成才,白天下地从事繁重的耕作,晚间边缫丝绩麻,边教子以大义,可谓含辛茹苦、忍辱负重。有一天,孔母终因劳累过度,晕倒在桑林。少年孔子为了侍奉好母亲为母分忧,停学帮别人操办丧事换取微薄收入,给母亲购买营养补品。孔母得知此事后,严厉训斥孔子,并告诫孔子要为母分忧就得学有所成。后来的孔子虽历经苦难,仍苦学勤思,矢志不渝。因此,孔母的形象在孔子心中是崇高的,孔子的睿智与伟大离不开母亲的抚养与教诲。
孔妻亓官氏:不甘清苦,抛夫弃子。古代文献关于孔子之妻亓官氏记载很少,只有三国时期王肃在《孔子家语》中留下了寥寥28字:“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,葬于防。至十九,娶于宋之亓官氏,一岁而生伯鱼。”另外,今曲阜之孔林中的孔墓,有人说是孔子与其妻亓官氏的合葬墓,但没有根据,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孔子葬礼时,只字不提亓官氏。其原因自然与亓官氏不甘清苦,抛夫弃子有关。孔子一生致力于自己的学问,一生为官时间短暂,经济拮据,加之多年游学列国,夫妻之间聚少离多。亓官氏不甘孤独清苦,更因看不到孔子的前途,抛夫弃子,离家出走。这件事对孔子的触动很大,女人也自然在孔子的心目中烙下了只可“同甘”难以“共苦”的印记。
宋公主南子:美艳淫乱,荒诞无耻。被史学界视为“美而淫”的南子本为宋国公主,后嫁给卫国为卫灵公夫人。据史料记载,南子貌美,作风不好,红杏出墙是家常便饭,而且尤喜玩弄权术。在宋国娘家时,便于堂兄朝私通,嫁给卫灵公后仍与昔日情人秘密来往。卫灵公知情后,不仅不斥责南子,干脆让南子把朝接到了卫国,来了个“三人同床”。南子深感她的夫君与自己“情趣相投”,更是肆无忌惮地与卫灵公的大臣弥子瑕勾搭成奸,时常淫乱。南子极其糜烂的生活不久就在卫国丑闻四播,朝野尽知。
时年五十六岁的孔子来到了卫国后,很快就接到了南子的邀请。按照子路的意见,孔子没有必要去拜见像南子那类名声极臭的女人。然在当时,孔子不去见南子还真的不行,于礼法不合,也有违孔子行事的风格:一是南子把持着卫国的政权,卫国的事情该怎么做她还真的有发言权和决定权;二是从外交礼仪上讲,孔子见南子应该且必须;三是南子是宋人,是孔子的“老乡”。孔子一向对故邦故国有深厚的感情,他临终前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的葬礼都是宋人的商礼。他之所以娶妻亓官氏,不单是遵母亲的遗愿,更因亓官氏是宋人,故而在异国他乡见见“老乡”南子也在情理之中。这一点我的观点倒是与南怀瑾先生相一致,南老先生说:“见南子就有不轨的行为吗?这是不可能的。南子虽然在社会上的名誉不太好,孔子也瞧不起她,到底她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夫人,她硬要见见,也理所当然。孔子特别讲礼,这又有什么失礼的?”故而,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孔子与南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,也没有必要为维护圣人的颜面而极力辩解。这样做都是徒劳的、无益的。
从上述的史料和论述,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:孔子一生中所接触到的三位女性,她们在品德性格上的巨大差异,给孔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,也制约着他对女性群体的评判。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,像他母亲那样的女性寥寥无几,如其妻亓官氏、卫灵公夫人南子一类的女性在那个时代和社会,似乎司空见惯。这或许是孔子得出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的原因所在。孔子此言的确说过了头,尽管当时“失德”女性不少,然相对于女性群体而言终归是少数。但我们应该予以理解和包容,不可凭此一句将我们伟大的孔子一棍子打死。
俗话说: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孔子虽是圣人,但他不是完人,他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血肉之躯,他的学问虽“道冠古今”,然总离不开受所处时代的局限,不可能是通天达地、通贯古今的全才。故而,当今之人一定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和思维方式,合理地评判我们的先贤,正确地裒判和运用先贤的知识和理念。
最后,我顺便来考据一下“养”字的字义。大多数的注家将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句中的“养”字释解为“蓄养”、“相处”字义。我认为不当,根据当时所用文字,应该从甲骨文字义,当释解为“管教”、“满足(欲望)”之意为宜。甲骨文“养”(见图)字字形左边为“牛”或“羊”,右边是“攴”,即一手执鞭,本义为“放牧”“饲养”,可引申为“管理”“管教”。《土生说字》:“‘养’从羊、从食,意为养生应从生理、心理和伦理三个方面入手,表明养生之道重在养心。”此说也有一定的道理。那么,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一句,可释为“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于管理和满足欲望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