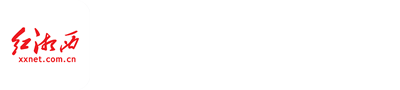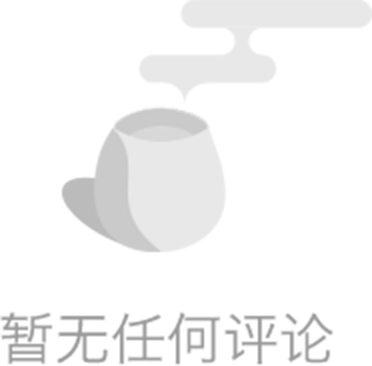诵读经典,从娃娃抓起。 滕 璟 摄
谭良田
李启群教授曾言及教留学生说汉语的一件趣事,那些洋学生纷纷惊讶地对她说,汉语像极了唱歌。李教授这句不经意的话,成为我二十年来思索与理解汉语的出发点之一。
某次语言文字学讨论会上,与瞿建慧老师谈到是否可以对当代歌词中汉字的实际声调作些研究,整理出其中的规律。瞿教授说,是个好题目,那得懂音乐学啊。当即我便沉默了。不管五线谱的豆芽菜,还是简谱上的洋数字,于我而言只是视觉符号,无法变现为声音。
我们每天说着汉语唱着歌儿,按理说唱歌于我们而言是天性,我却并不拥有唱歌的权利。每一首歌,必先由词人作词、作曲家谱曲,再经歌手演唱,到我参与其中,止于模仿。模仿,是我唱歌的代名词。当代中国,这个“我”,决非一人而已,是大多数,未经音乐学训练者绝大多数是。对于唱歌,我们已失了自主权很多年,剩下的,只有模仿。词人、作曲家、歌手,任何一人停止工作,我们便只有沉默而无新歌可唱,即便我们操着一种像极了唱歌的语言。
大学时的中国文学史课上,老师郑重强调,唐诗宋词乃至古文,本都是可以歌唱的。我们当即提议,老师,您唱一个!老师说,我没有古谱,怎么唱?那时我特价买了一套《叶圣陶全集》,知道叶老将唱诗唱词唱古文唤作“吟诵”。依老师的回应,我若有所悟,吟诵也是要歌谱的啊。
以上误解与困惑扰了我许多年。诗词古文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,困惑不解,如石压心。近两年,用心了解吟诵后,才知吟诵的歌谱本就藏在汉字的声音里,因此我们稀松平常的说话,在洋学生听来像极了唱歌。《尚书》说“歌永言”,永是“长”的意思,孔安国注云“歌咏其意以长其言”,即以长注永。可见,在古人看来,是个中国人,拉长了腔调说话,便是唱歌。理论甚是简单,可具体方法总归要人传授,自西方的“read”(现代朗诵)传入中国,这种传承中断了百余年,几成绝学。
吟诵的要义,是从汉字中生发旋律,形成曲调;而不是非得向豆芽菜或者洋数字讨要旋律。毕竟,我们仍用着汉字,说着汉语,只要能看着汉字发出声音,便依旧可以重拾生疏百年的乐感,从汉字中照见旋律,衍生曲调,重树我们唱歌的权利。对此,我们要有文化自信。
鲁迅曾说,汉字有“三美”,音美以感耳,形美以感目,意美以感心。从不同美感契入汉字,就有了不同的美之门类:意美感心则有文学,形美感目则有书法,音美感耳则有吟诵。古代的文人开口读书,必是吟诵;提笔写字,则是书法;研墨作文,即是文学。文人之所以唤作文人,首先得识字;识字怎可只认个躯壳?至少得从鲁迅所言三美领略其精神,滋养我身心,方可谓之认字,才能称作文人。
如何从音美感耳抵达吟诵呢?关键在声调!比如普通话有四个声调,根据声调高低起伏的不同,为它配上相应的旋律:阴平平着唱,阳平扬上去,上声拐个弯,去声降下来,这叫“依字行腔”。依字行腔,关键在“不倒字”。
啥是倒字?弄错了汉字笔顺,叫倒笔画;唱错了汉字声调则叫倒字。比如《生日歌》“祝你生日快乐”,祝的旋律就倒字了,按说去声要降下来,却层层递进平着唱了,于是祝字的实际声调就成了“zhū”。大学时某次生日会,我着实被朋友恶搞了一把,他们集体哄唱:“祝,你生日快乐!祝,你生日快乐!祝,你生日快乐!祝,你生日快乐!”待我反应过来,已是最后一句,无奈的反问道,我智商有那么低吗?
啥是不倒字?配上旋律后,汉字依旧方向性地保持其调性。比如普通话阴平的调值是55,吟诵出来可以是22、33、44,甚至是11;阳平的调值是35,吟诵出来可以是13、24、25,甚至15,总之是自下而上扬起来。上声去声,依此类推。
明白了“依字行腔”,理解了“不倒字”,与瞿教授讨论的问题也就有结论了,且无需为自己不懂音乐学而默声噤口,怯不敢言。吟诵不倒字,当代流行乐则惯常倒字。如“爱你一万年,爱你经得起考验”这句,不看歌词,还以为是“爱你一碗面,爱你经得起考研”呢。因此,当代歌词中汉字的实际声调,可以分为两类:倒字与不倒字。作曲家依汉字本调配上相应的旋律就不会倒字,所配相违则倒字。
依字行腔,可为单字分别配备旋律,然而其高低、快慢、长短、缓急如何形成,仍是个问题。别急,还有第二条,依义行调。
徐健顺先生《普通话吟诵教程》说:“每个字的唱法叫做腔,字和字的关系叫做调。旋律实际上是调和腔的结合。”也可以这样理解,单字旋律名为腔,成篇旋律名为调,有腔有调,叫做曲。旋律既然成篇,那一定得有高低、快慢、长短、缓急的变化,依据什么来决定这变化呢?依义!义,小则一个字的语境义,中则一句诗歌、一句文章的含义,大则指全文主旨、全篇意境。比如《夜雨寄北》是李商隐写给太太的回信,依据这一点,吟诵时要有相思之意,若吟诵得动感欢快,怎么可以?再如《古诗十九首》“行行重行行”连用五个平声字,表示渐行渐远,吟诵时必舒缓绵长,若唱腔抑扬顿挫,如何可行?
有了依字行腔、依义行调,便大抵可以度曲了。度曲是中国式作曲,学院式音乐训练对于度曲不是必须的;如果有,则可锦上添花。度曲的前提是识字,识字就要懂“小学”,包括三个主要学科:音韵学、文字学、训诂学,这于度曲来说,多少总要懂点,要够用。
学习中国诗创作,一般要从格律诗入手,学习吟诵也是如此。格律诗字与字之间的长短、高低是有规律的,这就是“平低仄高”“平长仄短”再加一个“入短韵长”,如此一来,格律诗的依义行调就只要考虑情感基调了。如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当持欢快喜悦心吟诵之,李商隐《锦瑟》似应以幽思感怀心抒发之,王昌龄《从军行》“青海长云暗雪山”要用雄强豪迈心歌唱之。至于平声字、仄声字、入声字如何分辨,这属于音韵学的基础知识,掌握并不难。
现代朗诵(read)传入中国百余年,蔚为大观无远弗届,这在洋学生听来虽仍像极了唱歌,可衡之吾人耳目,离唱歌总有未达一间之感。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》提出要“支持开展对吟诵的研究、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”,这是文化自信的彰显。中国语、中国文本具丰富的音乐性,依此而生的中国文学,更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生态关系。不关注音乐的维度,我们对自家文学的理解终究存有盲点。
吟诵,是重树我们唱歌权利的捷径。在自主的歌唱中,沿着音乐之维度进入中国文学,因其声美而观其意美,继而文字“三美”,尽收吾人心目。于是遨游乎这真文所开的大美世界,岂不快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