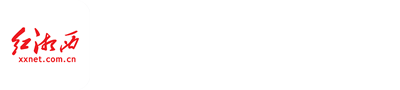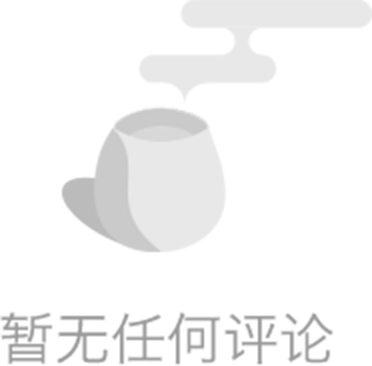—— 读《论语》及相关文献
周玉萍
《论语》简短,通俗,但是很耐读。
作为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、再传弟子言行的书,它重在客观忠实地记录,很少带有感情色彩,不下结论,也很少概括,像是课堂实录,或者是采访笔记。阅读者在孔子与其弟子的言谈举止之间,可以看到一堆大道理,也能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,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灵魂:温文尔雅、学问渊博的孔子,也有窘迫无奈的时刻;好学刻苦、安贫乐道的颜渊,堪称孔门弟子中才学与品德俱佳的“仁”者,可惜短命;聪慧练达的子贡,情商、智商皆为上乘,能够得钱财万贯,也能尊师如初……不过,其中性格特征最为突出、最容易“圈粉”的,当属子路无疑。
子路,名仲由(前542年―前480年),又字季路、季子。子路是鲁国卞(现在的山东省泗水县泉林镇卞桥)人,他比孔子小9岁,是最早跟随孔子求学、侍奉孔子时间最长的弟子。在《论语》中,子路的出镜率非常高。《论语》共20篇492则,有子路出现的共41则,有的以他为主角,有的有他参与,有的由他引出其他的人和事。孔子与子路的关系,是师生,更是朋友,之间有一段“相爱相杀”的过程。
《论语》中,子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鲁莽、轻率、心无城府,每次和孔子、师兄弟一起交流探讨,他总是忍不住抢先表达自己的看法: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:“以吾一日长乎尔,毋吾以也。居则曰:‘不吾知也。’如或知尔,则何以哉?”子路率尔而对曰:“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加之以师旅,因之以饥馑;由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……
—— 《论语·先进》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四人,是孔子门下才学较为突出、颇受器重的弟子。高徒在侧,孔子自然想乘机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内容。于是,他抛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:“如果有机会、有平台,你们希望实现怎样的人生抱负呢?”这个问题主观性强,怎么答都有理,但是要答出高度、得到认同,并不容易。一根直肠子到底的子路,在旁边全是“高人”的情况下,率先以洋洋自得的态度勾画了自己的宏大蓝图。不说其政见是否高明,其莽里莽撞的态度,在这场高手对决中,首先在气度上就输了。所以,孔子于不动声色之间,对其轻蔑地“哂”之。
《论语》中,子路挨骂的次数还有很多。
子曰:“衣敝缊袍,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,其由也与?‘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?’”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:“是道也,何足以臧?”
—— 《论语·子罕 》
子路出身贫寒,少时靠打零工为生,但他对外在物质条件并不看重,有“愿车马衣轻裘,与朋友共,敝之而无憾”的豪言壮语,穿着破旧灰暗的衣物,与衣着华丽的人站在一起,不会觉得心里受挫、自惭形秽,这是他的坦荡大气之处。那是因为他在乎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,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,所以十分在意孔子对他的评价。当孔子用《诗经·邶风》中的名句肯定他的时候,一向沉不住气的他,忍不住就自我陶醉、忘乎所以了,难怪会引来孔子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训。
子曰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,从我者其由与。”子路闻之喜。子曰:“由也好勇过我,无所取材。”
—— 《论语·公冶长》
子路为人好勇,入孔门之前是一幅“冠雄鸡、佩胡豚”的绿林好汉形象,后来在孔子的教导下穿上儒服,专心向学,但依旧将英勇视为自身的一大优势。听闻孔子将他视为远游避世的同行者,心里自然乐呵呵的。结果,却得到了一个“无所取材”的评价,可谓是贬入尘埃、毫无情面。
对待批评,子路是怎样的态度的?同为儒家经典的《孟子》,给出了指向十分明确的句子:
子路,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
—— 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
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就高兴,能够真正地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,将别人的批评视为勉励自己不断成长的良机。在对待自身的错误、对待中国人常常无法放开的面子问题上,子路同样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界。对其老师孔子不合“礼”、不符“仁”的言行,子路也敢于冒大不韪予以直言:
子见南子,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:“予所否者,天厌之,天厌之。”
—— 《论语·雍也》
公山弗扰以费畔,召,子欲往。子路不说,曰:“末之也已,何必公山氏之之也!”
—— 《论语·阳货》
在品德上,子路是一个值得敬佩之人。在才干上,子路虽然天资不算突出,与同门师弟颜渊、子贡等人相比,低了几个档次。但是他热爱学习,积极进取并马上付诸实践,执行能力超强。
子路有闻,未之能行,唯恐有闻。
—— 《论语·公冶长》
对待学问上,子路勤学好问,对于不懂或者存在疑惑的地方,喜欢刨根问底,知其然,更求知其所以然。《论语》之中,子路直接发问的,就有7则。他问政,问事君,问事鬼神,问成人,问君子,内容十分丰富,都得到了孔子的悉心指导。坦荡的胸襟,虔诚的态度,发奋的精神,让子路在孔子的熏陶教育之下,由“卞之野人”成长为识书达礼的君子。子路能够片言折狱,能治千乘之国,其为政的能力在孔门弟子之中较为瞩目,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识修为终于得到孔子的多方肯定。
子路性格直率,敢作敢当,豪迈直爽,对老师、对朋友能够做到忠诚担当,分享担当。若能够与他成为朋友,则不必因为“套路”而烦恼,不必担心背叛出卖,也不必担心一句话不对头而反目成仇,受难时有人相助,犯错时有人指正,苦闷时有人倾听,莫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?
可惜的是,可爱、可亲的真朋友子路,因为他的尚勇好义、直率坦荡,未得善终。
事情发生在哀公十五年,卫国内乱。之前出逃的太子蒯聩回到卫国想要复位,求助于卫国大夫孔悝。孔悝不愿意,蒯聩便直接挟持了他。这时,子路是孔悝的朝臣。事情发生的时候,子路正出门在外,听到消息后便急匆匆地回赶救急。路上遇到了同为孔门弟子的子羔,子羔告诉他:“国君已经逃亡,卫国情况很危险,你不能再进去了,免得白受牵连。”子路说:“食其食者不避其难。”随后,抱着大无畏精神进城去救孔悝。可惜寡不敌众,最终惨死在乱军的刀剑之下。
子路死前,有一个举动十分悲壮:混战之中,子路的帽缨被割断,他说:“君子死而冠不免。”他把帽子扶正,大义凛然地迎接死亡。
自古以来,关于子路之死的价值,有截然不同的判断。一种说法是,子路是鲁国之人,为卫国内乱这样一件本来与他没有关系的事情而死,死得莽撞,死得可惜,死得浪费;另一种说法是,子路忠于职守,为救主献身,值得钦佩,尤其是其大义赴死的气节,是君子所为。孰是孰非,自由各人去评说吧。
可惜的是,子路死后,这样的真朋友不再啊!